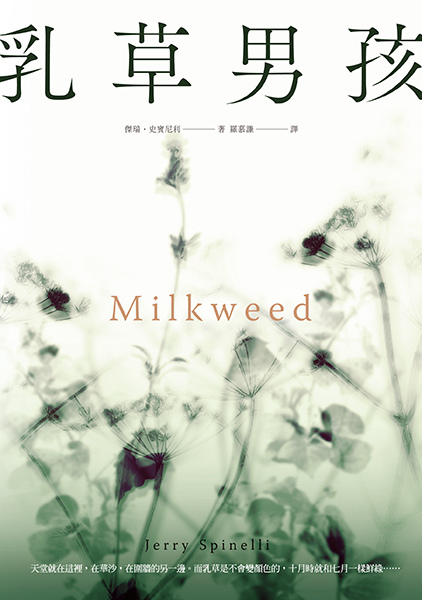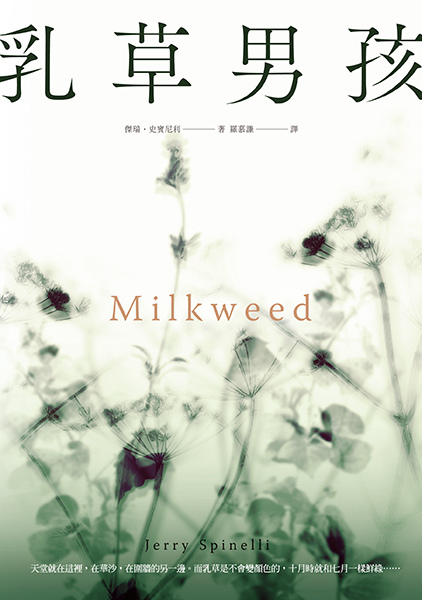
15 秋
人們在離去。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在街上走。我們站在一個街角觀看。
他們都是猶太人。我看他們手臂上的臂章就知道了。每個猶太人都要戴一個白底藍星的臂章。這樣一看就知道誰是猶太人,因為現在不是每個猶太人都留鬍子。在此之前,我只在這裡看過幾個猶太人、那裡看過幾個猶太人,從來不知道有這麼多猶太人。
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街道,但是他們全往同一個方向走去。小孩拉著小拉車,上面堆滿玩具、鍋子和書。大人拉著搖搖晃晃的大拉車,上面裝滿家具、衣服、圖畫和地毯。他們似乎把整間屋子的東西都清到大拉車、小推車及肩膀上鼓鼓的袋子裡。大的拉車由馬拉,小的拉車由人拉。馬和人看起來都一樣,緩慢吃力地前進,眼睛看著地面,被背上的負荷壓得彎下腰。馬沒帶臂章,但是牠們顯然也是猶太族。
那是一個藍白色的遊行──和大黑靴壯觀的遊行多不同啊!如此緩慢,如此安靜,幾乎聽不到有嬰兒在哭。成千上百隻大黑靴踏在地上的砰砰聲,現在變成了破舊鞋子拖在地上的聲音;坦克的隆隆聲成了推車輪子的喀喀聲。
我舉起手遮住陽光。「他們要去哪裡?」我問烏里。
「貧民窟。」烏里說。
「什麼是貧民窟?」
「命不好的人住的地方。」
遊行的人很安靜,但是遊行隊伍後卻有不少聲音。吹口哨、歡呼及打破玻璃的聲音。每次有猶太人從自己的房子走出來加入遊行,立刻就有別人衝進去。有些院子裡還有人在打架。人們從門口臺階上飛下來。頂樓的窗戶被掀開,屋子的新主人在遊行的人頭上大喊:「這是我的房子!」
但是我對貧民窟這個地方更感興趣,不論它在哪裡。「宵禁之前回來。」是烏里給我的唯一警告。
我加入猶太人一起走。有一會兒,我走得得意忘形。自從看過大黑靴壯觀的遊行後,就希望自己也能加入遊行。於是我跟著自己想像中的遊行跨步前進,超越一個又一個慢步前進的猶太人,頭抬得高高的,雙手擺動,正步前進,彷彿我也穿著又高又亮的大黑靴。如果有人用異樣的眼光看我,那我一定沒注意到。沒有人說一句話。很快地,我的想像就幻滅了,腳步也緩下來,像其他人一樣慢步前進。
我發現自己走在一個年紀看起來和烏里差不多的男孩旁邊。那男孩背著一個鼓鼓的大灰袋,像是裡面裝了南瓜。
「你認識烏里嗎?」我問。
那男孩不理我,只是瞪著前面看。
我提高聲量又問一次:「你認識烏里嗎?」
那男孩根本沒注意到我的存在。但我不是這麼輕易就可以打發。我決意繼續跟他講話。
「烏里的頭髮是紅色的。他不是猶太人。」我總是很小心不洩漏烏里的身分。「我可以摸摸你的臂章嗎?」他沒回話。我伸手摸摸他的臂章。「我是吉普賽人。」我說,「也許有一天我也會有個臂章。」
我從口袋裡掏出一條香腸。(只要我能找到香腸,我總是會隨身帶著它,然後有空就拿出來咬一口。)我把香腸伸給他,問:「你要咬一口我的香腸嗎?」這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眼睛動。但是走在另一邊的女士說:「他不餓,請你離開。」
真是不知感恩,我心想,但是我依她說的走開了。我從一個人走到下一個人身邊,不停地問:「你要去貧民窟嗎?……你在貧民窟會有個漂亮的房子嗎?……到貧民窟還有多遠?」但是沒有一個人回答我。我請每個人都咬一口我的香腸,但是沒有一個人要吃。沒有人看到我,或者至少我是這麼想──除了某些女士肩膀上的狐狸臉。牠們又黑又圓的小眼睛無止無盡地瞪著我看。